查看更多
密码过期或已经不安全,请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壹生身份认证协议书
同意
拒绝

同意
拒绝

同意
不同意并跳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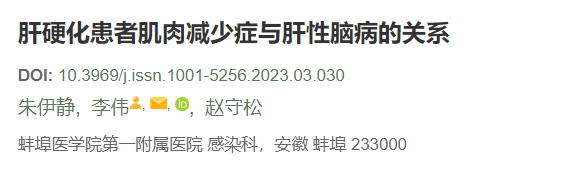

肝硬化患者HE的发生率国内外报道不一,可能是因为临床医生对HE的诊断标准不统一以及对轻微性肝性脑病(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MHE)的认知存在差异[1],其在整个肝硬化病程中发生率为30%~84%[2-3]。近年来,我国住院的肝硬化患者中约40%有MHE;目前国内外应用最广泛的仍是West-Haven HE分级标准,它将HE分为0~4级[1]。该分类标准对于0级(可能是MHE)及1级判别的主观性很强。近年国际肝性脑病和氮代谢协会提出的肝硬化神经认知功能变化谱分级标准中,将MHE和West-Haven分类0、1级HE统称为隐匿性肝性脑病(CHE);2~4级HE称为显性肝性脑病(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OHE)[1]。
MHE被认为是HE的临床前阶段,是肝硬化患者典型神经认知改变的一部分,虽然是亚临床的,但MHE与注意力、警觉性、反应抑制、执行功能、工作记忆力、心理运动速度以及视觉空间能力相关,因此可能被认为是肝硬化最严重的并发症[2, 4]。在一项临床随访[4]中,诊断有MHE的肝硬化患者随访3年累计进展为OHE占56%,且其他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显著增加。OHE恢复后,MHE可能持续存在。Nardelli等[2]发现MHE是OHE发生及其复发的明确危险因素,导致患者频繁住院。因此,临床的重点是在肝硬化等终末期肝病患者中筛查MHE,探究其相关临床意义。

肌少症既往被认为是与年龄相关的老年病,但最近有研究发现它是一种进行性疾病,往往与多系统疾病有关。目前已知关于肌少症的病因主要是与炎症、低活动量、低蛋白摄入和年龄等因素相关,在肝硬化患者中很常见。据报道患病率高达65%~90%[5]。根据2018年欧洲工作组更新的共识,肌少症是一组临床综合征,表现为肌肉力量下降,肌肉含量减少和躯体活动能力减退,导致残疾、生活质量降低,甚至死亡等不良后果[6]。尽管肌少症具有临床意义,但仍然缺乏肌少症的操作定义和标准化干预方案。肌少症影响因素较多,例如种族、体型、生活方式以及遗传背景等因素。其中种族是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种族人群有不同的标准。然而,亚洲由众多种族组成,选择合适的诊断临界值具有挑战性。目前可获得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东亚发表的。一项Meta分析[7]纳入了20个研究、4037例肝硬化患者,结果显示肌肉减少是肝硬化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且相比西方国家,亚洲人群肌肉减少相关的病死率更高。目前,握力是亚洲肌少症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肌肉力量测量方法,研究[8]显示:握力对肝硬化主要并发症和病死率有良好的预测价值。Wu等[9]提出了中国台湾的握力标准,表明中国台湾研究人群样本的平均握力明显低于来自主要为高加索研究人群样本的综合标准,肌少症诊断标准为:男性<22.4 kg和女性<14.3 kg。由于缺乏基于结果的临界值,2014年亚洲肌少症工作组建议在获得基于结果的数据之前,建议将低握力定义为男性<26 kg,女性<18 kg[10]。尽管在中国台湾发表的一些论文中使用基于欧洲老年人肌肉减少症工作组定义的肌少症临界值[11],但来自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结果建议使用男性<25 kg和女性<18 kg或16 kg作为临界值。我国2016年发布的《肌少症共识》[12]建议,静息状态下,优势手握力:男性>25 kg,女性>18 kg为正常,可排除肌少症。
随着肌肉质量评估仪器和方法的发展,基于横断面成像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可准确客观的评估人体成分。而且最近的欧洲共识声明已将CT扫描确定为诊断肌少症的金标准,尤其是测量第3腰椎间盘(L3)层面的肌肉横截面积[5]。而且L3横断面肌肉面积已被证明与全身肌肉质量密切相关,可准确地反映全身肌肉质量[13]。CT扫描获取L3横断面的单幅图像,使用HU阈值-29~+150对图像中的骨骼肌进行识别和量化,通过slice-O-matic或image J图像分析软件计算该层面肌肉的总面积,使用身高的平方归一化后,得到第三腰椎骨骼肌指数(L3-SMI)[5, 13-14]。目前,国际上应用较多的是来自美国的一项基于等待肝移植患者的数据[14],建议L3 SMI:女性<39 cm2/m2,男性<50 cm2/m2作为诊断肌少症的参考值。然而,L3横断面有不同组群肌肉组成,测量需要计算,相对复杂且容易出现误差。因此Durand等[13]通过CT扫描脐平面测量腰大肌轴向厚度,腰大肌是一种深层肌肉,腹水干扰偏差少,且易识别。再使用身高归一化后,得到TPMT/身高,用来预测肝移植等待名单上的肝硬化患者病死率。结果表明TPMT/身高是肌少症的客观标志物,而且是一个客观、连续和容易获得的变量,可以预测肝硬化患者的病死率,独立于MELD评分和MELD-Na评分。
然而,对于肌少症的精确定义尚无共识,北美专家意见声明建议仅根据骨骼肌质量进行诊断,而欧洲老年人肌肉减少症工作组第二次会议的定义包括低肌肉力量和质量进行诊断,定义低握力(男性<27 kg,女性<16 kg)[15-16]。在一项前瞻性研究中,亚洲肝硬化患者接受了连续的握力测试和L3-SMI测量,建议亚洲临界值为男性L3-SMI<36.5 cm2/m2和女性L3-SMI<30.2 cm2/m2[17-18]。亚洲人和白种人的身体成分差异使定义肌少症变得更加复杂,亚洲人的腹部和内脏脂肪量明显更高,肌肉量较少。2017年Carey等[19]研究队列中近30%的人为非高加索人种,其中黑人占5%,西班牙裔白人占11%,亚裔占8%,有趣的是,该研究并未发现种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然而无论使用何种诊断标准,肌少症患者的病死率均显著升高。因此未来的研究应以确定肝硬化患者不同种族的人群特异性握力和SMI临界值[20]。
一项来自孙超主任团队统计了414例肝硬化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21]发现,合并肌少症的患者,其HE的发生率明显升高,3年存活率显著降低,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肌少症是肝硬化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是临床上评估病情预后的可靠指标。
最近,我国陈煜教授团队[22]研究发表腰大肌指数作为营养状态指标,独立于MELD评分,可预测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长期病死率。腰大肌指数相对于SMI具有测量肌肉单一、测量面积小、边界清晰等特点,因此,测量更加简便且准确性高。近年来,肌少症指标由于其相对客观准确、可重复性强、受水钠潴留影响小等优点,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有望成为预测终末期肝病预后的重要标志物之一[22-23]。但目前研究阶段暂未对肌少症的严重程度具体分型,未来有待进一步研究。

支持肌少症和HE之间关系的病理生理学背景源于肌肉组织参与氨代谢和运输,氨在肝硬化认知障碍的发病机制中起核心作用。研究[3]发现,肌少症是HE发病的主要风险因素。肌少症患者HE的患病率比无肌少症患者高约20%,并且合并有肌少症的HE患者比无肌少症的平均生存期低约25个月。正常情况下机体降解氨的主要器官是肝脏和肌肉组织。肝衰竭和门脉系统分流受损发生时,肝脏降解血氨能力降低,此时由于骨骼肌组织体积及质量较大,成为氨解毒的主要器官,谷氨酰胺合成酶可能成为这一代谢过程中的一种重要酶[24]。在谷氨酰胺合成酶作用下将血清中的谷氨酰盐通过氨化作用生成谷氨酰,是除肝脏以外,另一种清除氨的重要途径。有研究等[25-26]发现谷氨酰胺在肝衰竭患者中具有重要作用。肌肉组织在氨代谢中起重要作用,肌肉质量和数量减少与HE风险增加有关。虽然骨骼肌减少和HE的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生物学联系尚不清楚,但肌肉组织可将血氨转化为谷氨酰胺,这一过程对HE患者的血氨清除具有重要作用。
一项临床研究[3]证实肌少症是发生HE的独立危险因素,且严重程度与患病率及Child-Pugh分级相关。当加入终末期肝病(MELD)评分模型时,肌肉改变已被证明可以用来提高对患者生存率的预测[2],肌肉改变后机体会容易疲劳,运动耐量降低,并可能会对日常表现状态和生活活动造成沉重负担[27-28]。多数研究证实了肝硬化患者的肌少症和OHE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但调查肌少症与肝硬化患者中MHE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多。目前查询到评估肌少症与MHE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研究总结: 在一项研究中,Merli等[29]对300例肝硬化住院患者进行了人体测量学评估肌肉减少、握力评估肌肉功能和神经心理测量学(PHES)评估诊断MHE,发现肌少症与MHE及OHE相关。在另一项研究[30]中,Hanai等根据生物电阻抗分析和握力评估,证实了MHE与肌少症之间的关联。还有研究[28]发现肌少症患者的MHE患病率高于无肌少症的患者,并且在多变量分析中,肌少症是MHE的独立预测因素。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多变量分析表明,进行数字连接测试A(用于检测MHE的测试之一)所需的时间与年龄、Child Pugh分级、营养不良和糖尿病呈独立相关。上述研究均未使用CT扫描来确定肌肉改变。一项前瞻性研究[2]使用CT扫描对肌少症进行定量评估,并使用PHES来评估认知障碍,以研究肌肉改变与MHE之间的联系。在这项研究中,肌少症与MHE的发生以及与随访期间OHE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发现L3-SMI评估的肌少症与PHES评估的心理测量结果表现之间呈正相关(更多肌肉=更好的心理测量结果表现),而L3-SMI与氨水平呈负相关[2-4]。近期Nardelli等[31]通过对114例肝硬化患者接受PHES和动物命名测试以检测MHE,腹部CT扫描用于分析SMI、肌肉衰减和自发性门体分流术。该研究表明:MHE、肌少症和自发性门体分流术在肝硬化患者中具有临床相关性,特别是,MHE和自发性门体分流术是与HE发生显著相关的危险因素,都与明显的HE病史显著相关。

高氨血症常见于肝硬化,在HE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肝硬化患者血氨的主要来源是由饮食中的含氮产物、肠道中尿素和蛋白质通过肠道细菌无氧酵解以及谷氨酰胺通过谷氨酰胺酶在小肠中脱氨而产生的,其中以具有脲酶的细菌为主,如肠杆菌科[1]。
当肝功能失代偿时,一方面肝脏对血清中氨的清除能力减弱,无法通过尿素合成去除血氨,血氨浓度增加,游离性血氨更容易透过血脑屏障,产生神经毒性,诱发HE。另一方面骨骼肌通过谷氨酰胺合成酶在氨代谢和清除中起代偿作用,这表明肌肉组织在氨代谢中起重要作用,肌肉改变与HE风险增加有关[26, 32]。近期发表的关于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后HE进展与肌肉改变的文章[33-34]提供了进一步证据,在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后,评估有肌少症的患者好转后获得了MHE的改善以及OHE发作次数变少,研究结果支持肌肉改变和HE之间的因果关系。肌少症好转的患者血氨也较前降低,并且观察到肌肉改变和氨循环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肌少症可能会导致循环血氨水平的增加,并在促进HE发生方面具有相关意义[35]。因此在肝功能不全的患者中,如果全身肌肉体积及肌肉质量降低,降低了清除血氨的替代途径,可间接导致HE的发生。对此,可以通过增加肌肉质量或控制血氨浓度减少HE的发生。
肌少症与高氨血症发生HE因果关系目前暂不明确。最近还有学者提出氨本身可能通过干扰蛋白质重塑而导致肝硬化患者的肌少症,进一步促进HE的发生,并且高氨血症会进一步恶化肌少症,他们之间存在恶性循环[36-37]。此外,Kumar等[38]研究表明,血氨通过上调肌肉生长抑制素的产生来损害肌肉蛋白质合成,肝硬化患者的血氨和骨骼肌中的肌肉生长抑制素表达增加。因此,高氨血症可能被认为是恶性循环的导火索:一方面,高氨血症的发生是肌少症的结果,因为消耗的肌肉无法代谢血氨;另一方面,血氨浓度的增加,导致进一步的肌肉消耗。

在肝硬化患者中,骨骼肌减少与HE显著相关,并有利于肝硬化患者HE的发展,但高血氨症是不是连接这两种疾病的唯一机制目前不明确。肌少症和HE有可能是肝功能低下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目前还没有充分证据来说明这一情况,亟需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探索[39]。这些观察的结果充分证明应考虑采取避免营养不良的措施,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减轻HE负担以及肝硬化其他并发症的可能性,这需要进一步研究[40-41]。在未来的研究中需继续探索清除氨的新方法和积极开展肌少症机制及诊治方面研究,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对肝硬化患者早期筛查和治疗,改善和预防肌肉改变,增强肌肉质量和力量,从而减少和预防HE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降低死亡风险。
查看更多